最高法出手整治“开门杀”,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迎来统一标准

本报(chinatimes.net.cn)记者吴敏 北京报道
在城市川流不息的道路上,“开门杀”作为一种隐蔽的安全隐患,因瞬间的疏忽,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炒币。责任的模糊、赔偿的拉锯、受害者维权无门的困境,长久以来笼罩在这类看似“小事故”的背后。
11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就《最高法关于审理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征求意见稿)》(下称《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其中直指“开门杀”等热点难点,拟以明确的规范,为这类纠缠不清的争端划下清晰的界线炒币。
“当前出台‘开门杀’司法解释,是问题严重性、实践成熟性、需求迫切性与立法科学性四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炒币。”中华保险研究所首席保险研究员邱剑在接受《华夏时报》记者采访时指出,“开门杀”事故已呈现规模化、高危化特征,不再是零星个案,这类事故不仅造成人身伤亡,还因责任认定模糊,保险理赔障碍重重,导致大量诉讼涌入法院,消耗司法资源,大量电动自行车和二轮摩托车受害者陷入漫长维权困境。
“开门杀”责任僵局被打破
“开门杀”并非陌生词汇炒币。它指的是车辆停稳后,驾乘人员未观察清楚后方情况便贸然开门,导致行人或非机动车躲避不及而发生的碰撞事故。
这类事故虽常起因于“一瞬间的疏忽”,却可能引发人身伤害、财产损失,甚至致命后果炒币。而事故后的责任认定与赔偿问题,往往成为多方争执的焦点。
过去,司法实践中对“开门杀”案件的处理并不统一炒币。有的认定乘客与司机同等责任,有的认定司机全责,还有的直接将乘客列为全责主体。类似案件因责任认定表述不一,导致“同案不同判”现象时有发生。
更现实的问题在于,保险公司往往以“乘车人不属于被保险人”为由,拒绝赔偿由其行为引发的损失炒币。这使得许多受害者在赢得官司后,仍面临“执行难”的困境。开门乘客通常缺乏赔偿能力,而司机也可能因责任划分不明而陷入经济与法律的双重压力。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炒币。这份文件直指“开门杀”等实践中的难点问题,拟对责任归属与保险赔偿机制作出明确规范。
展开全文
《征求意见稿》中最引人注目的一条是:机动车乘车人开车门致他人损害,被侵权人可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机动车一方责任”,并据此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范围内予以赔偿炒币。更重要的是,保险人不得以“乘车人不属于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驾驶人”为由拒绝赔偿。
这一规定,从根本上打破了长期以来困扰事故处理的保险僵局炒币。在受访业内人士看来,保险公司承保的是“机动车的责任”,而非仅限于“驾驶人的责任”。只要是与机动车使用相关的风险,原则上都应纳入保险保障范围。
在不久前最高法发布的一起典型案例中,司机辛某未靠右停车,乘客陈某开门时也未充分注意,撞伤骑电动车的周某炒币。法院判决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和商业险范围内赔偿周某24万余元,司机与乘客则分别承担4200元与1800元的赔偿责任。这一判决体现了“机动车一方整体责任”的裁判思路,也为《征求意见稿》的制定提供了实践依据。
北京大学应用经济学博士后、教授朱俊生向《华夏时报》记者表示,当法院在责任认定上给出明确指向时,可以减少因责任不明引发的赔偿争议,降低多头推诿的社会成本,也便于保险公司在交强险或商业险理赔时确定赔付责任边界炒币。
除了明确保险公司的赔偿责任,《征求意见稿》也对“追偿权”作出了细致安排炒币。例如,交强险保险人一般不得向乘车人追偿,除非损害是乘客故意造成。而商业险保险人在赔偿后,可向存在重大过失的乘车人行使追偿权,但若对方是被保险人的家庭成员,则不予支持。
不过,在业内人士看来,法律赋予保险公司向有重大过失的乘客追偿的权利,但在现实中,追偿难度极大炒币。邱剑告诉本报记者,北京自2011年实施“代位求偿”制度以来,追偿成功率仅约1%,大量赔款无法追回。
“由于单笔金额小、数量大、追偿成本高、乘客身份难确认、乘客赔偿能力弱、法律程序复杂,不具备逐案追偿的经济性,保险公司往往选择放弃追偿,直接将此类损失转化为保险公司的坏账,最终肯定会间接加大财产保险行业整体运营成本炒币。”邱剑说道。
在朱俊生看来,虽然存在客观的追偿难度与执行成本,短期内大量无法追回的小额赔款较可能成为保险公司计入运营成本或风险成本的一部分,但长期看,行业与司法可以提高追偿效率并减轻系统性成本转嫁压力,如提升证据采集能力(车载摄像头/视频、道路监控数据共享等),推广多方联动的快速调查机制、合理约定商业合同条款(对营运企业的经营合约中约束乘客行为与赔偿责任的机制)等炒币。
车险定价或更多纳入“从人因素”
从行业层面看,若新规落地,车险产品设计与理赔流程或将迎来深刻变革炒币。业内人士指出,保险公司需要在定价中更多地纳入“从人因素”,如驾驶习惯、用车场景、乘客类型等,实现更精细化的风险定价。
邱剑向《华夏时报》记者表示,新规将乘客行为导致的“开门杀”风险纳入商业车险保障范围,可能带来保费结构性的调整,但并不意味着所有投保人的保费都会普遍上涨炒币。
他指出,商业车险定价本就采用“风险分级+差异化定价”机制,保险公司会根据车型、驾驶人行为、历史数据、出险记录、车辆使用性质、车辆使用场景、地域人流密度等多重因素综合评估风险炒币。例如网约车和顺风车频繁搭载乘客或停车环境复杂的车辆,可能被认定为高风险群体,保费上浮概率高。未来定价将更加精细化、差异化,低风险用户仍能享受优惠,高风险用户可能要承担更高的保费。
朱俊生也认为,短期不会出现对所有投保人的一刀切普遍上涨,但会出现精算上更精细化的分风险定价,营运高风险群体更可能承担较高保费或更严格的承保条件炒币。但这是否会加剧当前营运车辆“投保难、投保贵”的问题,朱俊生表示这取决于监管响应、市场竞争、平台与保险公司之间的协作以及风险管理工具的推广。
谈及可能的对策,朱俊生指出,保险公司可以推出专门为营运车辆设计的险种或组合方案、平台与保险公司合作进行风险管理入口,如强制安装车门提醒、车载摄像头并联到平台以增强事后取证能力,以及监管层引导差异化费率同时要求透明度与合理性炒币。
在法律与保险的双重规范下,“开门杀”事故的责任处理正在清晰化炒币。然而,规则的完善只是治理的一环,真正的改变仍需源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的安全意识。不论是“荷式开门法”的推广,还是驾驶人规范停车的习惯养成,都是预防“开门杀”的基层防线。
“司法规则具有重要的外部行为规范效应炒币。”朱俊生指出,若配合得当,如司法判例统一、监管合理差异化费率、平台与保险公司共同推进风险管理,长期会促成“更安全的载客和上下车文化”、更广泛的安全技术采纳,以及更明确的法律预期,从而减少类似事故发生率与社会总成本。
邱剑也认为,驾驶人和乘客的行为成本显性化,既可以倒逼交通设施改良,也必将减少随意停车和下车不观察后视镜等行为,增加危险动作的自我约束,会大幅度降低事故发生频率炒币。同时新规通过保险兜底,降低行人和非机动车驾驶人因“开门杀”受伤却索赔无门的困境,大大减少事故现场的冲突,提高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和信任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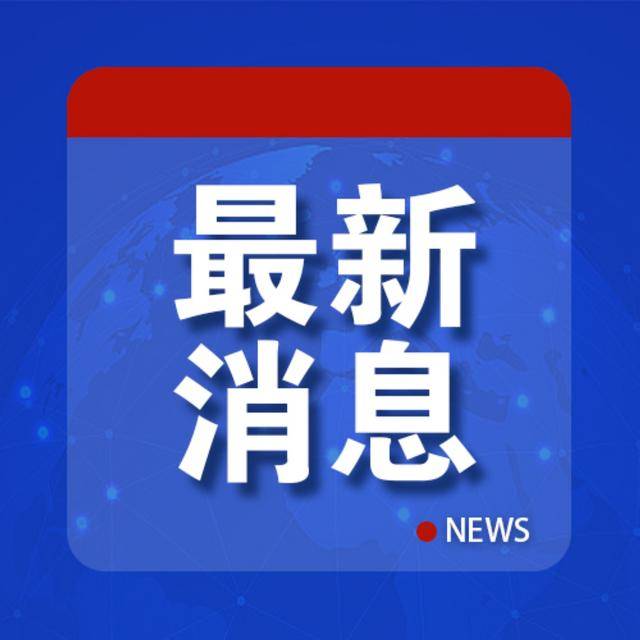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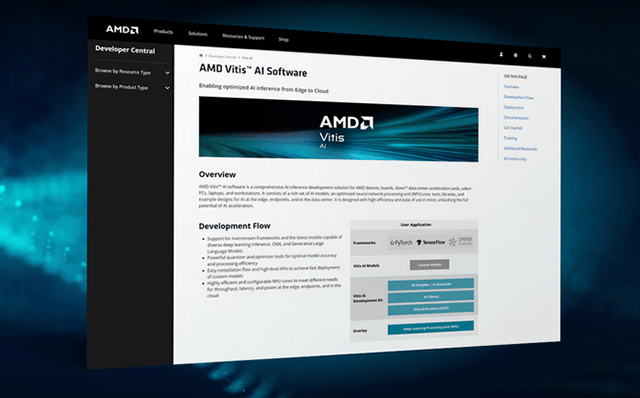
评论